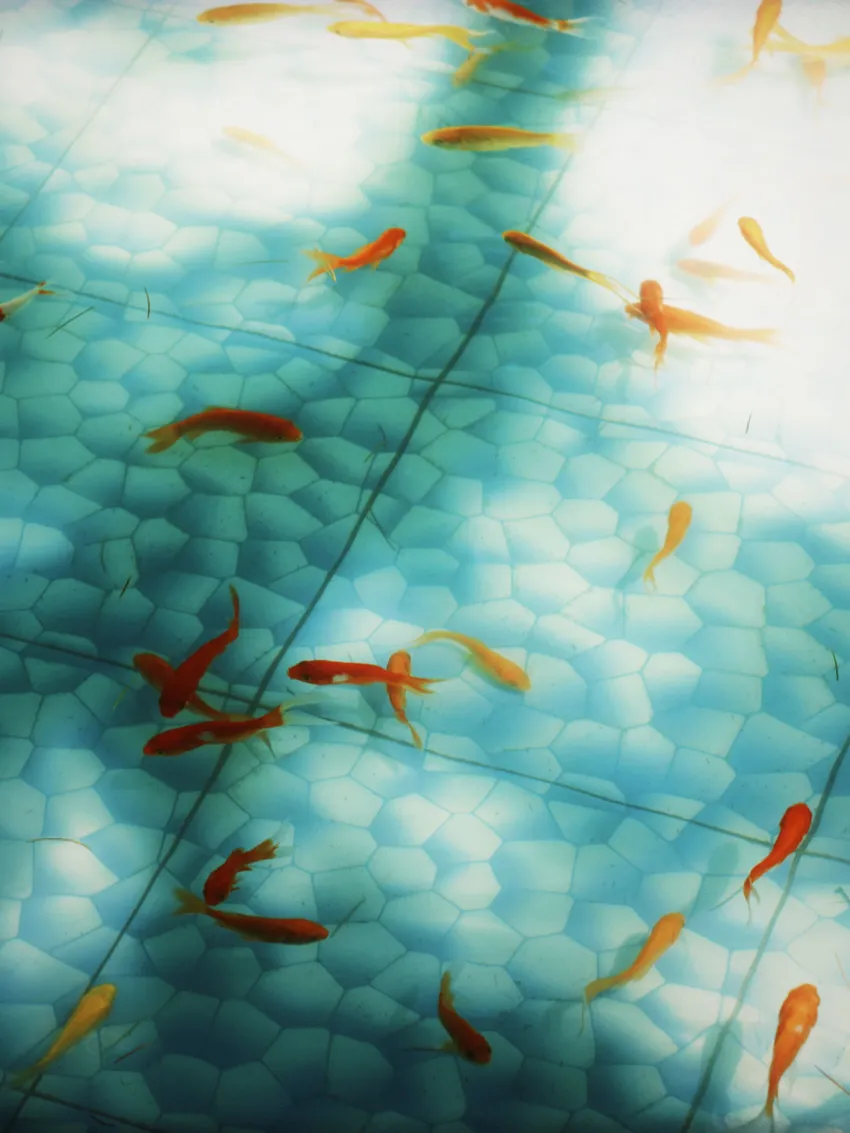【本文由小黑盒作家@墨下清风于10月27日发布,转载请表明出处!】
妹妹倏得拿起本年去的红山动物园。
这句话像把钥匙,旋开了顾虑深处某间尘封的房子。第一次去是八岁,当时关于独一雪糕棍那么高的我跟妹妹而言,红山动物园在我心里等于童话里的藏宝窟,是实验寰球最接近《动物寰球》的场地。
那然而动物园啊,等于央视九台,等于赵忠祥憨厚甘醇的嗓音,等于每天傍晚准时响起的《海尔昆季》主题曲。为此咱们本心得好几晚没睡平静,认为这比幼儿园组织的春游要高峻得多。
妹妹仰着脸问我:“哥哥,咱们确凿能去红山动物园吗?”她满含期待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我蹲下来平视着她:“确凿,不骗你。我和师傅齐陪你去。”
那是2006年的春天。爷爷从单元借了辆桑塔纳和司机,莫得导航,咱们举着一册绿色封面的舆图册就开拔了。早晨的雾气还没散尽,车子在轰动的乡说念上走走停停,每到一个歧路口齐要摇下车窗问路。等开到南京饱读楼病院时,已是中午。
消毒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和妹妹挤在贴满白色瓷砖的走廊里,蹲在冰凉的大地上。妹妹小声问爷爷:“咱们什么技巧去动物园呀?”爷爷摸摸她的头:“再等一忽儿,等师傅看完病就去。”
“可能是癌症”——大东说念主们柔声交谈的这个词,但没东说念主告诉咱们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下昼,车子也曾拐进了动物园。师傅走得很慢,妹妹因为晕车一直蔫蔫的,咱们其实没走多远,既没看到熊猫,也没见到老虎大象。
临了咱们在一个小广场的熊猫雕饰前合影。春天的风吹过草地,别的孩子在奔走嬉笑。而咱们一家牢牢挨着站在统统,用“生”的借口来袒护“死”的迫近。
回程的车上,妹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,呼吸轻轻拂过我的脖颈。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田园不知说念在思什么,那是我第一次清爽地感受到死亡在性射中的在场——它不在辽远,就藏在春天的阳光里,藏在妹妹纯确凿笑貌后,藏在咱们一家东说念主牢牢相靠的体温中。
好多年后我才显然竞猜大厅真人,阿谁春天的下昼,咱们看的不仅是动物,还在学习怎么与性射中的死亡共存。